原创短篇小说 皇室冲突
第六章“暴露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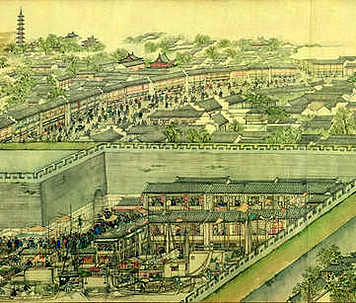
隔了三天,杜克又去了艾尔的房间,不过可怜的艾丽叶并没有再次被暗算——没这个必要。
因为有人看守,所以杜克不能轻易说话。
“嗯。”艾尔取出一本从埃德加那里弄来的维修用书,翻到目录,指着“加农炮”,点了点头。
“嗯。”杜克的眼神愈加坚定,因为这个消息是爱德华最后的“东风”。
“咔嚓”艾尔打开门,右手扶着门把,把整个上半身侧着往外探,张望着四周。
“要什么?”艾丽叶草草看向艾尔,因为她没法盯着艾尔的眼睛——玛丽的描述在艾丽叶的脑子里无限循环,使公主原本(对艾丽叶)的良好形象原地爆炸(主要是因为艾丽叶以为艾尔是跟她一样比较保守的人)。
“?”
“抱歉——有什么可以服务的?”
“没,谢谢,”又是一阵微风从艾尔脸旁呼过。“眼睛累了,看几分钟外面。”
于是艾丽叶又思考自己的事。
“不,玛丽说的不一定是真的,说不定是她梦到之类的……”她觉得自己懵的有些远了,需要一些理性的想法使自己醒一下。
“问一下情况不就清楚了。”她望着黑洞洞的枪口,“但这次是真的玩脱了,万一说漏嘴了怎么办?
“要不还是算了吧。”开始回忆以前有哪些自以为重要却又没插手,最后不了了之的事情。
但她想起来,她还有件事——很重要的事,上个月就想问了——这反倒坚定了她提问的决心。
“公主……昨天没怎样吧?”艾丽叶深吸一口气,集中注意力与艾尔对视。
“没啊。”艾尔感觉对方的眼神有些微妙,“如果出事了,你我都不会站在这里了。”
“不,我的意思是……”艾丽叶正拼命想一种得体的提问方式,但她失败了。
“您昨天没忘记做什么要紧事吧?”她突然意识到以她的身份,这个问题与之前毫无逻辑关系,于是又补了句:“最近记忆力降的厉害,老误事,担心……”
貌似更没什么关系了,于是艾丽叶止住了话头,尴尬地希望公主能一脸懵逼地关门进屋。
不过公主比她想象中更加耐心、热情:“不用那么紧张——我知道你想指什么——担心我忘了重要的事,对不对?”
艾丽叶就像个五岁小孩一样,十分乖巧地点点头。
“让我想想,昨天……”眼珠绕着眼眶跑了一圈又一圈,弄得艾丽叶又不想跟她对视。
“好像……”小脸一红,“忘记锁门了。”
“诶,我以为就我会这样……”沉闷地叹气,“还是……”
“我还有事,先进去了。”艾尔表情变得凝重,迅速关了门。
“不是吧,我什么都没多说啊!”狠狠踢了一脚墙,把左手搭在双眼上,“这下怎么解释?”
“不是吧……干得这么隐秘都能发现?不可能啊!”艾尔尝试着用旁人的眼光,把信件看了一遍又一遍, “这怎么可能看得出什么端倪来?”
但艾丽叶已经确确实实警告过自己了——说不定埃德加已经知道了,正准备抓自己呢;而艾丽叶还把自己当半个友人,不想我死前才悔恨自己的自作聪明哩!
“如果是我会错意了呢?”艾尔还是不肯相信自己“暴露”了,“没锁门可以导致很多破事。”
“但这种事情没有万一,万一就是呢?”迅速收好信件,再取出一张新信纸,写几个字,想了想,划掉。
“没时间弄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了,必须通知爱德华提前进攻日期!”
社长 原创短篇小说
(本故事多取自现实,然情节纯属虚构,请勿当真)
文学院在学校里,是不很大的学院,在学校几万人的学生里,文学院只有两三百人,而它的名气,和别校的中文系与文学院办法比,就是和人数最少的某一专业比,它的名气也不可思议地要低上许多。虽然老师多很有水平,为人也都很好的,却总不见学院又好转的迹象,甚至朝着越发低下的方向不可逆转地跌了下去。学校曾经承诺给院里搭建新的办公楼,老师们很开心,想着终于能从那偏僻的上个世纪便已投入使用的楼里搬出来,幸喜地准备迎接新楼时,电气院的人却神不知鬼不觉地搬进去了桌子,人也多坐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椅子,这倒让文学院的老师觉得尴尬了,于是就去求,但最后像是没有成功,至今没有个结果。但别人都认为这是没什么的,毕竟既然被叫做文学院,那么他们只要有放小说的地方应该就够了,这样的理解,倒让做语言学研究和古文学的老师十分恼火,研究文学史和文化研究的老师也多是很悲伤的。
文学院的社团是在老师们坐了几年旧楼的桌椅后才成立的,具体是什么时候成立的,我也说不清楚,但我想到社团目前已印发了十八期杂志,想着它应该是在十八年前创立的。是的,我这里已经说出来了,我们文学院的社团并非是什么文学同好读书会(即便我们确实有组织读书会的活动),而是做了杂志。学过现当代文学史的各位都十分清楚,报刊杂志的推广作用究竟有多么重要,而缺乏地位的文学院,自然要靠着它来点亮自己,但文学院是没有闲钱的,以至于拨款总是不很够,摆脱不了专业的杂志社,于是,便决定自己搞杂志,至于杂志的名字,便取了“树深时闻泉”这个名字,简称为“闻泉”。
我小学时,本喜欢读鲁迅的作品,经典的几本读完后,便没有了读书的兴趣,直到了高一,受了语文老师的点播,这才又开始读起书来,看起了巴尔扎克、余华一类人,也对写作颇有兴趣,以至于在高考前夕,我依旧在读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,同时又在做题之余抽空写起小说来。后来读了大学,进了文学院,听说了这么一个社团,便兴致勃勃地加入了。也是在加入社团后不久,我便见到了社长。
社长当时还不是社长,不过是编委会中的一个副编辑,当我之后也担任了相同的职务时,我才知道这个位置所要做的便是征稿和审稿。他当时和我们见面,本意是想着举行一场互评会,在申请入社团时,大家都提交了各自的创作稿件(大家对自己所创作的作品水平心知肚明,没有人会自大到将自己的文字作品称做是“书”,更没有人会自大到称自己为“作家”),这会儿便都拿出来,要我们互相评价。他在讲台上做互评会的说明时,我便注意起他的样貌:头发短平,似乎刚刚洗过,但总显得有些油腻,小小的眼睛藏在圆框眼镜后头,与之不相称的是他高大结实的块头,而他紧绷着的笑容下,似乎藏着孕育已久的紧张。他在快速解释完毕用意后,教室便陷入到长时间的沉默之中,我低头看着手机上印出的文字,看到作者那栏陌生的名字,隐隐约约想到这是和我同一届的同学,便又努力想着作者的脸,最后才会去看到下面的文字内容——现在想来,那是一篇颇有先锋味道的文章,不过视角处理还是显得幼稚,不过当时的我却是十分喜欢。
在沉默将整个空间凝结之前,社长便决心做出改变。他自己先开了头,说:“这样吧,我们就挑一篇文章,来谈谈各自的看法。先选......”他这里顾自找了一会儿,“先选蒋明晓同学的作品吧。”他选到的这篇,便是我看到的这篇。我虽然十分内向,这会儿却有了莫名的勇气,举手示意要发言。“这篇文章很有余华九十年代前‘黑暗时期’作品风格的味道。”我用当时我所知道最为专业的说法做了回答,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是叫做“先锋文学”的。接着,我又挑文章里面的几点说了几句,便草草结束了。在我之后,又有一位同学举手做了发言,接着,便没有人再举手了。
社长一时不知道该怎么继续,便又换了话题,说:“其实,你们交上来的作品我们都看了,其中有很多写得不错的作品。像是季行穷写的《白原马》,还有沈林星同学写的《大侠》......”这里,我听到了我的名字,以及我的作品,整个人都精神许多,而这时他又自言自语似的补了一句,“这部作品写得是真的十分厉害。”我记得,那是一部有关伤痕文学的作品,本来是为调侃某个网络写手所写的《我不是大侠》,便做了《我是大侠》,以嘲讽他作品之低劣,只是在之后的创作中,却又想到了许多点子,这才成了一部伤痕之作。现在想来,那文章是十分拙劣的,对于历史的反思因用力过猛而失了真,内容也多剽窃余华《兄弟》的影子,语言也总模仿余华,又没有那自如的感觉,总体而言,并非是部优秀的作品。不过他当时这般评价我,还是让我觉得十分开心。
互评会最后还是在尴尬之中结束,这样的互评会在之后也没有再组织过。那次会后,社长找到了我,对我说:“我很看好你。”在半年之后,当我加入社团编委会,成为了他的同事之后,他对我的评价依旧是这样。
我在半年之后加入编委会这件事,其实并没有多么的了不得。因为学业上的繁忙,加之其余学生组织工作任务的加重,原先加入社团的新生们纷纷不再参与社团的活动,以致连每月固定要交的稿件都无法交上。作为依旧按时交稿的几人中的一员,所交稿子又多是几千字的小说,我便顺理成章地加入了编委会。事后,社长提起这件事时,他总要恨恨地说:“他们要不愿意参加,那就不要参加!”这倒和他那天互评会上的形象完全不一样。
记得和我一同加入编委会的,是我同班的一位男生,以及同班的一位女生。男生叫魏雨泽,是个强人,读过很多书,又看得杂,社会学的作品也经常有看,他每次发表观点时,不时会引用些理论性的知识,而他所提到的人往往是我不曾听闻过的人;女生叫李蓉,她和我本是没有什么交集的,毕竟文学院男少女多,平时我的社会交际无非是同五六个男生有关,是很没有理由去和她交流的。当时,我们三人被邀请到了学校的食堂,陆续到了以后坐了会儿,社长一行人才再赶到。除了社长外,到场的还有两位学姐,这三人一起,组成了迎新团队,而我当时还不知道,这三人便是当时编委会的全部成员了。社长见到我们,很不见外,就这么坐了下来,说:“欢迎各位加入编委会,我们现在很缺人手......”这便是全部的欢迎仪式了。紧接着,他往我们各自手机上发了些文件,里面装着的是征文活动的投稿。“咱们现在看一看,决定一下哪些能过。”社长说完,便低下头去看稿件了。我们这就算是开始工作了。
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那第一次的审稿经历。那次的稿件,总共分了九个专题,除去第一个专题外,其余部分都有几十篇稿件。第一个专题是关于赞扬建国以来的我国所取得的成就的,但投的稿件大多没什么水平,其中写得相对最好的一篇,是一篇古体诗,而社长对它的评价,则是气愤的一句:“这个人根本就不会写诗!我们要把这篇交上去,老师和学姐们会骂死我们的!”便一篇都不打算要。接下来的几个部分,便是社长主导做分析,其余人发表各自意见,再一致表决。社长的分析总是很有道理,他总能看出稿件里存在的不足,“这篇诗完全就是在堆叠意象,没有一点逻辑的。”“这诗连格律平仄都是不对的!”“这篇散文写得太做作——散文是贴近生活的真实的。”“这篇小说太网文了。”“这个人,是我们院里的大佬,你们学习一下她怎么写的......”那时的我还完全不懂评判的技巧,发表自己意见时,总不能很好地表达,说的话也多没有说服力。稿件中有一篇写“丧”文化的现代诗,被社长批评为“他想要表达什么?”“现代诗也是要讲音韵的。”于是决定把它除去。而我个人却颇喜这篇诗,便要争论,想着把它留下来,但我说的理由,只是“我知道它要说什么。但我说不清......只可意会,不可言传......”大家都没能听懂我的意思。社长发了话:“你是生活中有着相似的体会吗?”我点了点头,于是他又说,“那就先待定吧,我们继续往下看。”
那次审稿是从六点开始的,而当食堂灭了灯,准备关门了,我们才粗略地审了一半的稿子。我看了眼自己的手表,发现这时候已经十点了。于是,大家都站起身,走到食堂门外,各自道了别,商定了下一次审稿的时间,便都散了。走在回宿舍的路上,我只觉得自己的眼睛有些发痛,可心情却是十分愉悦的。我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燃烧着,而并非在电脑屏幕前僵硬地冻着,我头一次觉得时间的消耗是件如此令人开心的事。
社团的工作总是间断地进行。平时没有工作,便像平时一样,在电子产品里消磨自己的时间,或是试着和郁达夫、曹禺一类人对话,再花些时间去背诵先秦两汉时期的诗与赋;当有了工作,也不是很忙碌,只要抽些空闲时候,花上几个小时便可。这悠闲的样子,在我进入大二,成为了社团的管理人员之一后,同样没有改变:我所做的不过是征稿和审稿,和负责读书会筹办的魏雨泽比起来,是很没有什么的;至于要兼顾一切的社长,便是更为辛苦的。
大二的一天,工作毫无预兆地来了。这次的工作,是要置办社团的杂志。在我加入杂志社后,时过一年才有杂志的消息,这令我十分惊讶,而事实便是,出于某种我至今都没能搞懂的原因,杂志的编撰中止了一两年的时间,新一期的杂志现在才刚刚开始动工。而在开始动工后,我才发现了又一事实:审稿时,原先陪同着社长的两位女生不见了,而李蓉同学也不见了踪影。事后我才了解到,那两位女生早已不做了工作,社长这会儿才成了真正的社长,而她们连同着李蓉,再之后的活动中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审稿的工作又成了三个人的事。
审稿时,社长的脸板得比平时更为严肃,几个小时下来,话也不说几句,只是在表决的时候,说声“好”“可以”“再想想”,于是主导的工作交给了魏雨泽同学。他看得书多,但看问题不比社长要精确,很多写得不错的文章,到了他眼下,几十秒便看完,然后被打上“不行”的话语,扔到了一边,除非我这时提出我自己的看法,否则他不会又任何的反悔。
三人的审稿氛围并不怎么好,效率也很低。社长看不下去,又招了个新人,是个叫陈上的女生,平时很活泼,谈论时也很积极,虽然见解不一定十分正确,但确实让氛围显得不那么压抑。不过,四个人的审稿效率依旧不高。面对比先前任何一次都要多出许多的稿件数量,我们的工作进度缓慢异常,直至大二第一学期末,这事儿才有了结束的影子。
我们审最后一部分稿时,社长将地点安排在了宿舍园区的一家咖啡厅里。我到他包下的房间时,几个人已经都坐好在了座位上,眼前都摆着电脑,上面开着的是装着稿件的文件,桌面的中央是几盘小吃,这会儿被动过几下,但没有动多少。我随便挑了个就近的位置坐下,这便开始了审稿的工作。
因为马上要解决这个困扰了社团许久的问题,大家表现得都很轻松,审稿的过程中有说有笑。社长中途给大家点了茶,各自喝了几杯,都觉得很不错;一篇写得颇为滑稽的现代诗摆上了台面,大家觉得作者实在没有水平,便都笑起来;魏雨泽又很快地看完了一篇四千字的小说,着急地做了“删了!”的决定,惹得陈上和社长叫喊着反对;拟定版块版名时,我自以为巧妙地用写作用笔和饮品做了搭配,结果被社长吐槽是“让杂志成了菜单”,于是他自己找了几句诗句,大家都为之叫好。等一切都要安排好了,社长便又点了一份华夫饼,叫我们各拿一块,沾了奶油和蜂蜜吃了,边吃,他边说:“我下半年之后也要忙起来了,到时候,社团就得靠你们了。”语重心长地说了十分钟的话,这才继续原本的工作。
所有的文章都已敲定,大家的心情都很愉快,接下来,只需要找到文章的原作者以及他的联系方式,确保证书与奖品可以准确送达,这事就告一段落,剩下的就是和负责技术编排的同学联系就行。但是,由于这些稿件多是一两年前的投稿,很多作者的联系方式都从都被丢在了某个人电脑的一角,于是,我们便从社团的公共邮箱入手,想着原邮件里找到些信息。可是,当我们打开邮箱时,却发现里头并没有我们想要的稿件。我们看到前几页堆着近几个星期学院发来的通知文件,而到了后面,邮件的日期突然就跳到了三年前,中间那段时间的邮件居然不翼而飞了。我们呆坐在座位上,只有社长开始联系起所有知道这个邮箱的同学,而在得不到任何有效信息后,他又打电话给了负责邮箱管理的客服电话,询问了半个小时,却还是一点正面的消息也没有。他放下手机时,脸拧成了一团,血液都流向他的大脑,脸颊被血烫得通红。我们坐在一旁,一句话也不敢说,一个动作也不敢做。过了好一会儿,他才看向我们,缓缓说了句:“都回去吧,大家,明天再说。”
往后的时间里,我们成员之间再没有了联系,编委会的群聊里,已经很久没有人发消息了。突然有一天,我在前去吃午饭的路上,猛地想起这件事来,这才意识到这事已经一两个月没有消息了。我于是感到焦虑起来,心想自己居然连这么大的事也不记得了,于是鼓起勇气,去找了魏雨泽,和他谈起了这件事。他听了我的话,先是一惊,说:“哦,这件事!”一副出乎意料的样子,接着便摇摇头,说自己不清楚。我们俩又找到了陈上,跟她说了这件事,她听了我们的话,原本笑着的脸突然严肃起来,说了一句:“这件事......”她似乎也完全忘记了这件事。
到了这个学期期末考试接近了尾声,我们只差几门考试便到了假期时,突然,编委会的群聊中有了消息。那是社长发来的消息,他上传了一篇文章,下面附上一句“我朋友发的,看看能不能让我们帮忙发到网上。”,接着又加了一句“你们看看怎么样”。我点开那篇文章,阅读起来。那是一篇十分晦涩的文章,先是讲了一个从远方到来的朋友,又是讲自己对课上老师所教内容的各种思考,再有谈到那个朋友,而在文章最后,文章又一转先前的悲愤,转而写到了自己对另一个女生的爱慕。但纵使这般,我依旧读懂了作者的意图:那是一种情绪的宣泄,所有的回忆,所有的情绪,都在这篇作品里喷发。我看到文末那个女生的名字,深知那是前社长名字的化名,于是,一种近乎同情的悲痛从我心里钻了出来。我回复社长说,这是一篇情绪化的文章,写的都是作者的真实。过了一会儿,他只回了一句:“你说的很对。”便不再有消息了。
假期结束,我再一次返校,又再一次上课。一天,我用着剩下的闲钱去了咖啡店,点了杯燕麦牛奶,又点了份提拉米苏蛋糕,找了个偏僻无人的座位,看起了老师所布置的《静静的顿河》,突然,一股莫名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。我抬头环顾起咖啡店,眼睛不自主地锁定在了一间包厢。那是我们平时进行读书会的地方,我们在那里探讨了《为什么速度越快,时间越少》中的“加速”,探讨了《族长的秋天》对于独裁者与其体系,探讨了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》,以此追忆陈寅恪先生与其“精神”和“思想”,以及其他种种。而这会儿,一个年轻人正坐在那儿开心地聊着天,几个人拨弄着手里的吉他,而几个人又在一旁唱歌。我想到了些什么,又明白了些什么。这时,牛奶和蛋糕都端了上来,摆在了桌上,我却没有要开动的心情。我把手里的书摊开放在桌上,模糊地想起翻开的那几页上写着的是本丘克被枪决时的场景。我感觉自己成了葛里高利,这会儿,却希望自己成为波乔尔科夫。
|原创短篇小说、皇室冲突
原创短篇小说 大学社团 小说 文学 皇室冲突 社长